缙云丨陈朝权:老屋记忆

老屋记忆
文/陈朝权
老屋,装着我最美好的时光,是我生命的根基,是我岁月的沉淀。每当夜深人静,我总会想起故乡的老屋。
一天清晨,微风拂煦,我和三弟乘坐侄儿的小车,从县城出发,向阔别多年的老屋疾驶而去。进入村子,只见昔日弯来拐去的土坯村道公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。我们沿着村道向前行驶,遇见公路两旁干活的乡亲,侄儿马上踩下刹车,我们下车去与他们打招呼。这是父辈留下的礼仪,我们几代人都遵守。
大约十点多钟,到达了生我养我的地方,这里是我的老屋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,受地理条件限制,老屋无法拓展,姊妹们逐渐长大,居住越来越困难,父母决定另外选址新建,举家搬迁。虽然时过境迁,但对这里的一切,依然历历在目。
我清楚地记得,当年这个院子呈“门”字形,住着大爸、二爸、三爸和我们家。他们住的是木结构房屋,各有三间。我们住在端头,屋旁有一条大路,上学的学生、赶集的村民都往这里路过。我家房屋墙体用泥巴筑、屋顶用青瓦盖,只有一间,中间设隔墙,前部分作厨房和餐厅,后部分及楼上设床位并放置装有粮食的坛坛罐罐。全家九人生活在这间屋子,拥挤不堪,就连萝卜也只好放在屋顶,红苕存放在屋后竹林地窖。院子后面是一片树林,有竹子、柏树、桃树、李树、柑子树等。院子中央有一块青石板铺的坝子,坝外有一个水池,池中常有成双成对的鸭子游来游去,给院子增添一道美丽风景。
老屋旁边是集体保管室。在农村合作社时期,集体劳动都是统一开工,统一收工,生产队记工员每天按时在保管室附近吹出工号和收工号。保管室前有一块由集体修建的大石坝,用于集体晒稻谷、苞谷、麦子、高粱、豌豆、胡豆等粮食作物,晒干后进入保管室由生产队保管员保管。每到夏天夜里,石坝周围院子的多数人家都到坝子里铺上凉床,劳累了一天的大人们一边乘凉一边摆龙门阵,孩子们在坝子打闹嬉戏、藏猫儿,坝子里充满欢声笑语。有一年夏天,石油钻探队来老屋附近钻探,在保管室宿营。我从未见过钻探石油的场面,出于好奇,经常跑去现场观看,一来二去,与钻探工人们熟了。一天夜里,我和父母正在坝子乘凉,他们从稻田里捉来许多黄鳝,开肠破肚后红烧,突如其来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坝子。当我发呆似地感受扑鼻而来的香味时,一位讲普通话的工人叔叔走过来,叫我去与他们一起享用。对于一年吃不上几次肉的我,毫不客气。一边吃着美味佳肴,一边聆听他们给我讲故事。他们为了祖国建设的需要,常年东奔西跑,日晒雨淋,到处钻探寻找石油资源,有时夜以继日。他们四海为家,与家人聚少离多。他们那种务实作风和奉献精神感动了我、激励了我,暗下决心:长大后发奋读书,成为他们一样,为建设祖国做贡献。
保管室旁有一棵几百年的黄葛树,树冠巨大,枝繁叶茂,夏天结果,鸟儿在树上筑起不少鸟窝,叔叔阿姨们习惯夏天在那黄葛树下享受荫凉。哥哥是爬树能手,时常上树掏鸟蛋回家大家一起煮着吃。如今,那棵历经几百年风吹雨打的黄葛树岿然挺立,树叶迎风舞动,像是优美的舞蹈,令人心旷神怡。
站在一旁的三弟指着老屋前的那块地说:“二哥,你还记得不?那个地方原来是垃圾堆,哥哥为了减轻家庭负担,将那里平整成一块地,再把别人卖甘蔗丢弃的甘蔗尖捡回栽在那里。由于土质肥沃,甘蔗长势良好,既粗又甜,拿去场上很快卖完。”我说:“当然记得,哥哥用卖甘蔗的钱买回几只小鸡饲养生蛋,即使如此,我们也只能在生日那天才能吃上一个鸡蛋。因为平时的鸡蛋要积累起来卖钱,然后用卖鸡蛋的钱买回盐巴、煤油、火柴、针线等生活必需品。”
回忆到这里,我和三弟都觉得我们小时候真是不懂事,父母和哥哥姐姐那么辛苦,而我们成天只图好玩。记得小时候,经常邀约附近院子的伙伴到我们院拍方块、踢毽子、滚铁环,尽享那份简单而纯粹的快乐。玩到天黑,回家喊肚子饿了,要妈妈煮面条。当母亲开始向碗里挑面条时,几姊妹围着锅台,目不转睛地盯着油渣。油渣只有一两个,几姊妹都想吃。为了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感觉委屈,母亲边挑面条边笑着说:“小孩吃不得油渣,吃了会长蛔虫。”于是,我们都不争吃油渣了。我们长大后才知道,那是母亲善意的谎言。
大爸、二爸、三爸的家庭条件比我们家好,他们宰了年猪,都要给我们端来一大碗香喷喷的回锅肉。回锅肉的味道是亲情的味道,混合着柴火与炊烟,温暖着我们的心房。每到春节前夕,家家户户都将糯米和糯苞谷按一定比例泡一大盆,几天后磨细晒干,用于春节煮汤圆。正月初一早上,我们四家都要相互赠送一碗汤圆品尝。我们家的汤圆制作得更加精细,他们品尝后常常赞不绝口。那时候,我们院子相处和谐,气氛融洽,感觉每个瞬间都充满人情味。
7岁那年,父亲将我送到完小上一年级。完小设在我们村。每天放学回家后,下午完成父母安排的割草任务,晚上在煤油灯下做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。在老师的精心辅导和自身努力下,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,连年获评“三好学生”,父亲将我每次获得的奖状贴在老屋墙上,引以为荣。小学三年级时,老师动员我跳级,父亲没有同意。他说:“还是一步一个脚印,稳扎稳打好。”
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,不知不觉自己已到花甲之年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念旧情结越来越浓。我和三弟禁不住围绕老屋周围逛了一圈,感觉变化翻天覆地。堂兄们建了楼房,煤油灯早已退出舞台,每家每户用上电灯,有了彩电,几乎人人都有手机,多数家庭买有小车,保管室坝子变成了免费停车场,唯一没有变化的是老屋院子里的青石板地坝、老屋后的竹林、果树和旁边几百年的大黄葛树。
走过风雨沧桑,依旧怀念在老屋生活的日子。那青石板地坝,那斑驳的老墙,让我无法忘怀。在老屋度过的日子,是一段温馨的岁月,是一份纯真的回忆。我留念老屋的时光,那时候虽然贫穷但快乐,邻里之间互相帮助,亲情友情无比真挚。
中午时分,我们在老屋所在院子与堂兄及其儿女共进午餐,似乎回到了当年。吃饭间,聊起陈年往事。我说:“当年我家太穷,父母担心我们娶不上媳妇!”堂兄的女儿立马接过话题,笑着对我说:“二叔,我们现在还记得你和二婶耍朋友的故事。有一次,二婶在家里唱歌,您把盆子当乐器,有节奏地敲打,逗得院子的人哈哈大笑!”
饭后,堂兄硬要我们在他屋前的柑橘树上摘些柑橘带走。他说:“你们是这里土生土长的,这柑橘有家乡的味道,你们一定要带走。”按照堂兄的吩咐,三弟和侄儿摘了三袋放进车里,然后握手道别,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老屋。
回到城里,思绪仍旧飘向故乡的老屋。
作者简介:陈朝权,机关干部,重庆市荣昌区作家协会会员。先后在《中国金融》《金融时报》《建设银行报》《中国建设报》《重庆金融》《红岩春秋》《巴蜀史志》《重庆地方志》《重庆历史名人》《巴渝人文》等报刊上发表作品。
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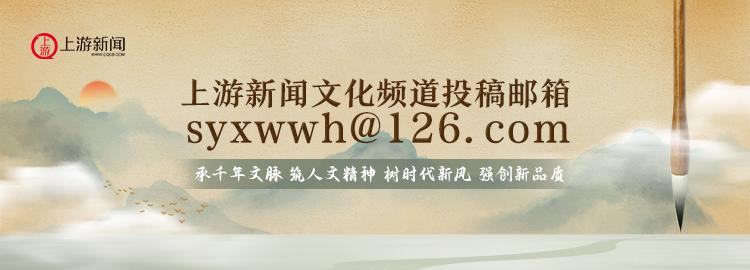
编辑:朱阳夏责编:李奇,陈泰湧 审核:阮鹏程